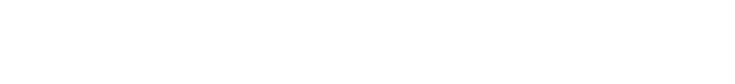范成大的槟榔情缘
范成大(1126—1193),字致能,号石湖居士,平江府吴县(今江苏苏州)人,是南宋著名的政治家、文学家和诗人。他出身书香门第,父亲范零为宣和六年(1124)进士,母亲蔡氏乃北宋名臣蔡襄的孙女、宰相文彦博的外孙女。自幼受家庭文化熏陶,范成大十二岁遍读经史,十四岁能文。然而父母早逝,使他身心受创,一度寄居寺院,以读书吟咏自遣,远离科举十余年。后得父亲友人相助,于绍兴二十四年(1154)中进士,步入仕途。历任知处州、静江府兼广南西道安抚使、四川制置使,终官至参知政事。他曾出使金国,抗争不屈,几近遇害,晚年退隐故乡石湖,以诗文名世,著有《石湖居士诗集》《石湖词》《揽辔录》《吴船录》等。
范成大的一生与南方风土结下不解之缘,尤其是他与槟榔的“相遇”,更成为其文学与笔记中一段生动的记忆。这种缘分,既源于其宦游经历,也体现了他作为文人的好奇与实证精神。
乾道八年(1172),范成大自苏州出发,赴任静江府(今桂林)知府兼广南西道安抚使。途中,他以日记体写就游记《骖鸾录》,详细记录了经江苏、浙江、江西、湖南至广西的见闻。这部笔记不仅山川古迹、风物人情悉备,更以“事核词雅,实具史法”(清人周中孚语)著称。正是在这段旅程中,范成大第一次深入接触到岭南食槟榔之俗。
甫入桂林,他便为当地地貌所震撼:“平野豁开,两旁石峰森峭,罗列左右,如排衙引而南。”然而更令他惊异的,是道上的“鲜血之点凝渍”。他初以为乃屠宰牲畜所遗,然“怪其何其多也”,经仔细察究,方知是嚼槟榔者所唾之汁。这一发现,被他以纪实的笔法写入《骖鸾录》,成为南宋时期槟榔民俗的珍贵记载。
范成大对槟榔的记述并未止于好奇。在《桂海虞衡志·志器》中,他专设“槟榔合”一条,详细描述槟榔的食用方法与器具:“南人既喜食槟榔,其法:石灰或蚬灰并扶留藤同咀,则不涩。士人家至以银、锡作小合(盒),如银铤样,中为三室:一贮灰,一贮藤,一贮槟榔。”
这种精巧的容器,反映了槟榔在南方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——不仅是日常嗜好,更是待客之礼、婚聘之仪。范成大以近乎人类学的眼光,记录下这一风俗的物质文化与社交功能。
事实上,槟榔在岭南的历史悠久。南北朝时《南中八郡志》已载,当地人以槟榔为待客佳品,“婚族好客辄先进此物”;《九真蛮僚俗》亦云,婚俗中“以槟榔子一函诣女,女食即婚”。同为南宋学者周去非《岭外代答》更明确写道:“客至不设茶,唯以槟榔为礼。”范成大虽为北人,却以开放的心态观察、记录这一习俗,甚至试图理解其背后的文化逻辑。
值得注意的是,范成大对槟榔的态度是复杂而辩证的。他既客观记述其俗,也不避讳其“唾如脓血可厌”的直观感受。在诗《巴蜀人好食生蒜,臭不可近。顷在峤南,其人好食槟榔,合蛎灰、扶留藤,一名蒌藤,食之辄昏然,已而醒快。三物合和,唾如脓血可厌。今来蜀道,又为食蒜者所熏。戏题》,诗曰:
旅食谙殊俗,堆盘骇异闻。
南餐灰荐蛎,巴馔菜先荤。
幸脱蒌藤醉,还遭胡蒜熏。
丝蓴乡味好,归梦水连云。
他调侃自己“幸脱蒌藤醉,还遭胡蒜熏”,以幽默笔触写南北饮食之异,介绍南方人食槟榔的方法,揭示出槟榔对非习服者的强烈刺激。
范成大之所以对槟榔如此关注,与其身份和使命密切相关。作为地方大吏,他需深入了解民情风俗;作为文人,他又具备记录与传播的自觉。他的槟榔叙事,不仅是个人的见闻笔记,更成为后世研究宋代岭南社会的重要史料。透过他的文字,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种嗜好品,更是一种文化符号——它联结了南北、沟通了士庶,也折射出宋代南方生活的鲜活图景。
范成大的槟榔情缘,是士人传统与地方知识的相遇,是实证精神与文学笔法的交融。他虽未如当地士人那般沉醉于槟榔之甘,却以笔为镜,照见了那个时代一方风土的真实面貌。这种以文记俗、以史存真的努力,正是范成大作为南宋杰出文臣与学者的不朽所在。
(何银坤 供稿)